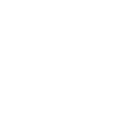黎肖嫻(Linda Lai)是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School of Creative Media,下稱SCM)的副教授,教出不少學生,雖為學者,書寫過不少媒體歷史、民俗志、電影與都市研究等論文,她同時是一位以研究主導創作的跨領域藝術家,其作品形式多樣,包括實驗錄像、數碼或混合媒介的裝置、衍生性藝術等。間中她亦會客串,以策展人之姿為一些較小眾和實驗性的理念策劃展覽,組織學生或志同道合的人成立一些團體,如2004至今還活躍的「文字機器創作集」 (Writing Machine Collective)或2015年以來的「據點」(Floating Projects),鼓勵大家繼續創作與發表作品。她總是孜孜不倦地探索著自身與世界的關係,在理論、實踐、教學、創作中自得其樂,思考著藝術的奧秘,並把她的發現與學生或觀眾分享。
是次採訪以問答方式進行,Q & A如探戈,透過了解Linda的硏究及創作經驗、由她的起點走進本地媒體藝術的世界,讀者可以多種角度去思考本地藝術發展的脈絡,以及展望未來的可能性。

Q:你與藝術或媒體藝術接觸的起點是怎樣的?
A:這個故事太長了,而且這是由於被問及才會被構築和述說出來的故事。我從來不會計劃任何事情,頗為隨緣,沒有特別原因去決定自己要做什麼。我從小就會畫畫,興致到來就扮演粵劇花旦造手。讀中小學時,總能輕鬆完成美勞課的習作並得到讚賞,這些東西種在一位小朋友心裡,會讓一個人知道,原來做某些事情不需花太大的力氣。這不是指喜歡做的就多做一點,而是有一些事情是自己擅長與不擅長的,費力與否其實頗為重要,所以一路走來,我並非特意去培養自己的藝術造詣,例如有人建議我去學鋼琴,家人說沒錢,那就算了,但參加合唱團是免費的,就去唱,一直都很隨遇而安。
Q:這是對藝術的陶養,那你跟媒體藝術的接觸點在哪呢?
A:這跟音樂的興趣和訓練有關,其次是我對文學的興趣,Experimental Literature (實驗文學)是很重要的切入點,當我四周尋找資源的時候,音樂的知識讓我可以繼續開拓,不過後來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副修藝術的經歷並不愉快,我當時本來決定這輩子都不會從事藝術相關的工作。
Q:為什麼?
A:當時我副修藝術只想畫畫,不明白評分的準則,雖然覺得那不太重要,我的心早已經向著實驗劇場飛去,四年的英文系主修課裡,我演了三年默劇,這亦跟音樂有關係,它講求組織時間、節奏,還有身體的力度、雕塑、結構等。
Q:那你後來為什麼會選擇去美國修讀電影研究?
A:因為我又被相關的東西吸引住了,我的訓練培養了我對文本的重視,於是開始留意大眾媒體,即是電視。當我回顧媒體歷史,特別是在外國,才發現原來跟電視有著密切關係,這是我當時並不知情的。我是一個極之好奇的人,加上有文學和音樂的支援,每當有新的藝術形式出現時,不會毫無頭緒,可慢慢尋找線索,釐清我與世界的關係。
Q:回顧你的媒體藝術歷程,當中有沒有一個轉捩點或特別重要的時刻?
A:我在1998年加入SCM,1999年我們才開始招收第一屆本科學生,回想起來,才知道這是非常重要的一環。當時學校的氣氛比較開放,甚至SCM的使命是甚麼,都是不斷熱烈討論而衍生出來的;當時一個來自UGC(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重點,就是SCM的存在使命不是成為一所電影學院,而是當時的人還不太瞭解的「多媒體」研習。作為一個初生之犢的學者,我對這個挑戰很興奮,覺得一片新知識的領域正在等待我,而且,那時候我心裡早已對剛成系統性知識的電影研究產生很多懷疑。當時我很欣賞的一位副校長Professor Edmond Ko(1952 – 2012),批出了不少撥款作拓展教學之用, 讓我們可做更多實驗性的教學,促成了我的起步。當時,也有兩位同事Mike Wong(王健明)和Hector Rodriguez(羅海德),運用了這批資助成立了「Invisible Lab」,這項目與他們的教學有關,我去旁聽那些課堂,與其他學生一起聽課,那對我是很重要的啟發。
Q:這些課堂具體都教些什麼?對你有何重要影響?
A:我本來是文科生,從來不怕數學卻沒有機會進深,那時候突然接觸到non-Euclidean geometry,思考invisible space(隱形空間)或higher dimensions(更高維度)這些概念,又第一次認真了解M.C. Escher的畫作,大眼開界,還有其他古怪的空間如Fractals、Torus等。這些科目都極具實驗性,雖然當時覺得只有理論沒有實踐,仍然大有啟發。我認為媒體藝術是有其理念上的底蘊的,背後的「慾望」更重要,不能一開始就跳步到用電腦軟件或編碼去玩弄創作。
Q:那麼我們可否這樣形容:SCM剛剛創立時,是老師跟學生一起探索的過程,因為你也是初初接觸到這些理論?
A:這(Invisible Lab)以後,我花了大量時間按自己的能力去認識new biology(新生物學),還有modes of automation (自動化模式)、chaos theory(混沌理論),還有emergence(演生)、self-organization (自我組織)等與進化論有關的觀念,構成了我的第一個實驗教學課程:什麼是「機器」(machine),新生物學如何翻新了「機器」的定義等問題,然後放進實驗文學裡去做實作的實驗,過程中我一直思考的automatism(如不假思索文字創作),接連簡單的數理操作如permutation and combinatorials,以至音樂中的序列式創作(serialism)。到後來,這個運作了兩年的SM2220 Writing Machine 課就重新命名為SM2220 Generative Art & Literature (衍生性藝術與文學)。
我並不認為自己在媒體藝術裡,尤其是對技術層面的教學有何貢獻,這令我更集中於做一個歷史學者 ,這個最初的起點延續成我對某些現象背後和物理過程產生了興趣,但我是以藝術工作者的角度出發,而不是一個專家的角度。舉例說,2003年後,我將自己做過的小實驗變成一些我能力範圍所及的事。如automatic writing (自動書寫) 是我的強項,但若放於媒體藝術的過程裡,我們該探討的是如何去處理和整合隨機性;若要強化不可知和發現的驚喜的話,那就需要coding (編程),這並非我本有的訓練,但當中又有某些事我可以做到,如對敘事的思考,會有音樂元素在。Combinatorial organization (組合式組織)、permutation(排列)等這些關鍵字,經常在我的作品描述裡出現,換句話說,我會就著數個基本元素,運用不同的方法去組織,讓作品可以永遠延伸下去,或者擁有一個無限的壽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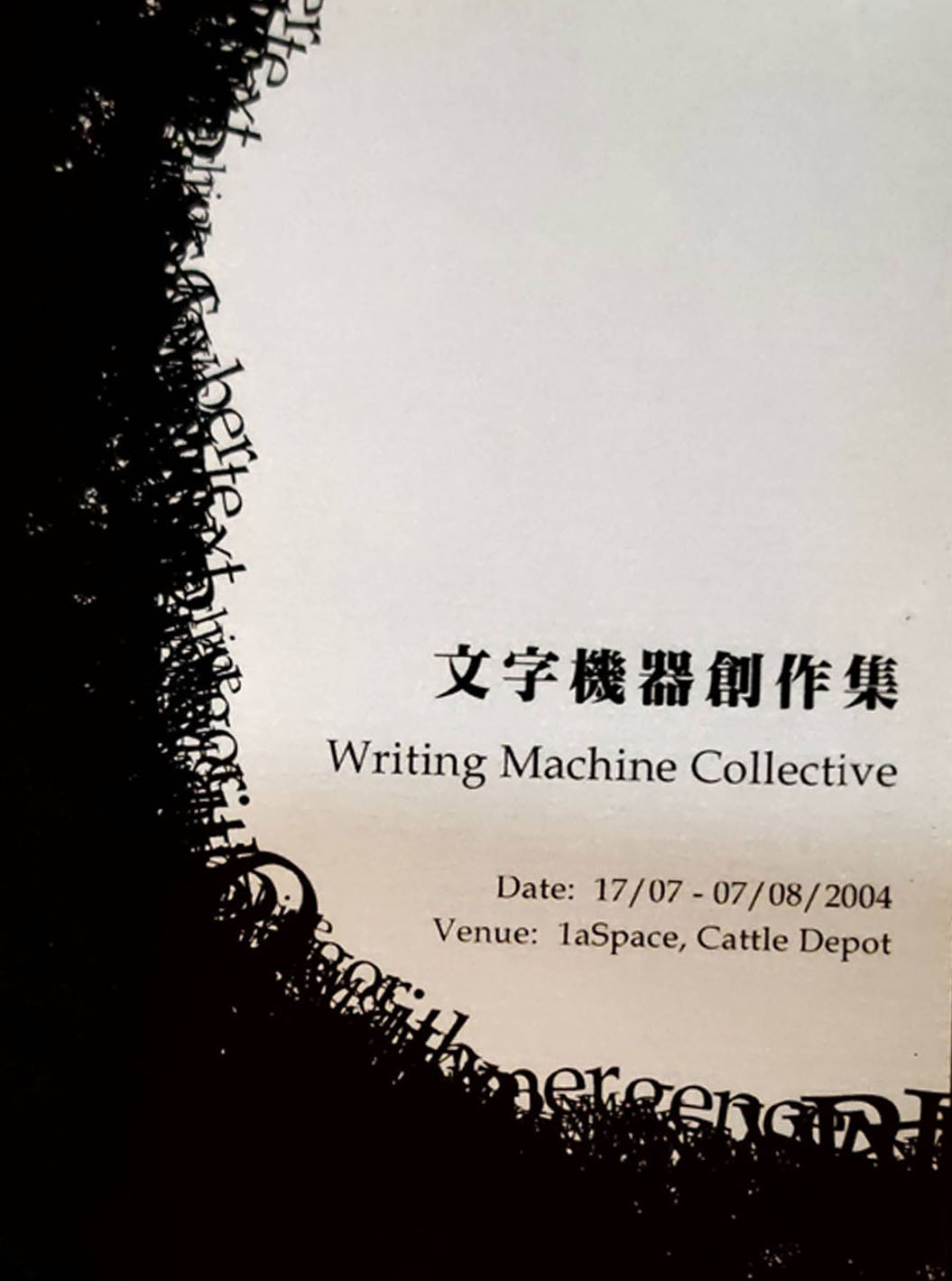
“Writing Machine Collective I”「文字機器創作集」第一辑 Jul-Aug, 2004, 1a space, Hong Kong.
Q:這是不是「文字機器創作集」背後的理念?
A:對。我把教學和創作實驗當中的一些概念獨立出來,如透過簡單原則怎樣可構成複雜事物,試試會否召集到一班有相近興致的人。簡單而言,如第一期的「文字創作機器集」,2004年時因為研究撥款的支援讓Ray Chan和Keith Lam(林欣傑)可以參與SM2220的助教工作,以至發展「文字機器創作集」的第一集,展出的基本上全是學生作品或該科目的內容。當時的困難是要利用Director Lingo 和 Flash ActionScript等軟件創作一些展出兩星期而不會hang的作品,做到那已經很有成就感!因為我們之前根本沒試過這些東西。當時作品的內容較為簡單,全都是輸入一首詩或一隻字,那個字又會衍生出其他字,扣連成文學實驗創作的成果,幾好玩。
Q:根據你過往任教SCM的經驗,你有否察覺到學生們當中有世代之別 ?他們都沉浸於不同年代的科技裡,新一代媒體藝術家是否有著不同的特質?
A:很難一概而論,只不過當時除了SCM之外,沒別的地方有同類型的聚焦的訓練,如我們經常遺漏了香港專業教育學院(Hong Kong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又稱IVE ),事實上,他們在軟件技術上是非常專注的,較為技術主導。相對的,SCM比較概念性,以人文的心態去創作。
Q:相較之下,現在的學生技術層面是否好得多?
A:環境已經改變了。SCM最早幾屆面試學生時,若有人懂得製作網站,已經非常難得。近年SCM錄取的學生都比較慣用各種軟件,但我並不覺得大家的技術起步點提升後,會令他們變得更有創意或具有實驗精神。可以說我一直沒有離開「技術vs創作」這掙扎,如在三年制大學轉四年期間,我們推行的課程中,讓文學士課程的學生去修讀編程相關的課程,便惹來了很多爭議,直到今天仍然有同學和老師對此感到質疑。畢竟,要大家相信「編碼」是重要的新語言的話,還要費不少唇舌。 這也和中學教育文理分割滋養了先入為主的恐懼有關。
Q:是面對了很多反對聲音吧?
A:是的,但我們不能放棄,我們要訓練的學生是為了未來,而非現在。於不久將來,要是不懂得以簡單的電腦編程制定一些指令,根本沒辦法在這麼複雜、 數據主導的世界裡生存。這不是說編程很厲害,而是它某程度上是一種語言,如學生以這心態去學習的話,便會接受自己學了一兩年仍未足夠。這個爭拗仍會持續──應不應該取消文學士課程中的編程科目?我常常思考,我們是否只教學生們喜歡的課?身為教育工作者或課程設計者,我們有沒有遠見?跟同學討論時,其實有一半人是被說服了的,他們知道若有這項技能,會開拓他們的創作空間,可以做出更多東西。

Q:你怎樣看現今觀眾對媒體藝術的反應?對媒體藝術的未有否任何願景?
A:期望大家能夠配合彼此的想法,以達成一個共同方向,並以之去理解媒體藝術的話,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為什麼要有共同的方向呢?藝術的世界本來就那麼多樣化,媒體藝術同樣會是多樣化的,並不可能變成單單一種方向或兩種方向。在大數據時代還要分門別類什麼是媒體藝術什麼不是,我總覺有點落後,但也要討論下去吧。
就算是Microwave(微波國際新媒體藝術節),我有時並不特別滿意,雖然過去它已有不少貢獻,特別於某些年代,它讓大眾接受媒體藝術或吸引到觀眾,已經做得很好。但我亦感到去到某階段,單純看展已沒太大用處,這亦包括我自身的反思,我們從來都是與一群專家或是圈內人士討論,是否沒太大作用?怎樣能夠吸引其他人去參與,而不是光光走馬看花?
這思考並非單單指Microwave或其他以電腦為基礎的媒體藝術項目,亦包括我一直沒放棄過的錄像藝術。正如我最近籌備的Videozine (錄像誌)《平地數碼》,揀選得獎作品時,我突然想去奬勵一些欠缺相關拍攝背景的人,因為我感到他花了很多力氣去訴說一些故事,我們是否應該「打開」?並不是去找更多觀眾,而是開放創作者是誰的觀念,或他們可以表達何種內容的空間。我們該做的,是打開一些話題,打開一些媒體創作階級的等次,把它鬆開之外,我很想運用較為簡單的方法跟不同人分享我們所做的事。
在這階段裡,我思考的並非一些大型項目,市面上已有不同機構和專才在教育上、創作上做得非常出色,我反而在思考一些較為微細的東西。我對媒體藝術的期望,是對藝術的期望——更開放,更刺中存在的要害,令人感到藝術有存在的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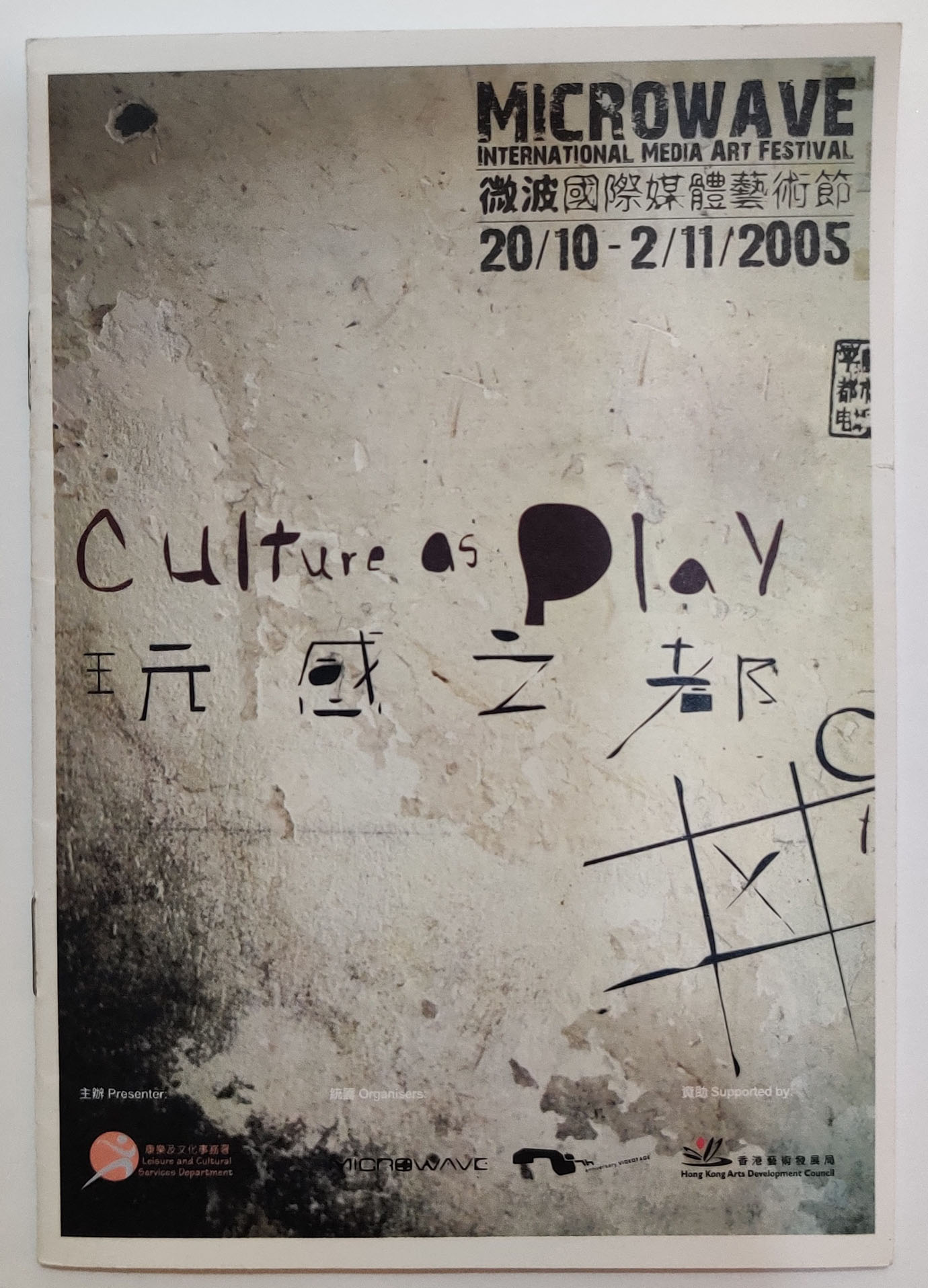
Culture as Play《玩感之都》, Microwave International Media Art Festival 2005.
黎肖嫻於紐約大學電影研究系取得哲學博士,她的作品是其藝術和理論研究的伸延。她是一名跨領域藝術家、媒體考古學家、實驗藝術倡導暨策展人。
黎肖嫻曾擔任跨領域媒體藝術展覽《演算藝術:劃破時空》(2018 – 2019)的策展人,也是以香港為基地的新媒體項目「文字機器創作集」(2004)的發起人,積極探討電算思維與當代藝術之間的主題,至今已發表六輯聯展。她從女性主義的觸覺思維出發,將批判理論,圖像理論和敘述性融為一體,並探問:藝術在史學中的具體作用是什麼? 其蒙太奇藝術及實驗性裝置曾於歐美和亞洲多個城市展出,部分數碼作品更被北京廣州錄像局、香港的M+收集存檔,其中由第九屆上海雙年展(2012 – 2013)委託大型混合媒體裝置,現成為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永久收藏。
「據點。句點」為其最新的實驗計劃,探索藝術群體組織的模式以及藝術創作、組織的持續性。2018年5月,她獲頒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家年獎(媒體藝術) 2017」。
Linda Lai Chiu-han’s artistic and scholarly works extend her PhD training in Cinema Studies, New York University. She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artist, media archaeologist, and advocate curator for experimental art.
She curated “Algorithmic Art: Shuffling Space and Time” (2018-2019) on art and the sciences, and founded the new media art “The Writing Machine Collective” in 2004, with six published editions of research-based group shows. Her feminist sensibility entrenches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practices, integrating Critical Theory, image theories and narrativity, asking: what is art’s specific role in historiography? Her montage art has been featured in various international art events, including solo features at Pearl Lam Galleries, EXiM, EXiS and C3A Spain (2021). Her digital works are archived and collected at the Video Bureau and M+, and large-scale commissioned installation for Shanghai Biennale (2012-2013) at Power Station for Contemporary Art.
Floating Projects is her in-depth, on-going participatory art experiment. With the Floating Projects Collective, she realizes D-Normal/V-Essay on-line video zine for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HKADC)’s Arts Go Digital. Her scholarly writings account for the genealogies of media and video art and Hong Kong’s screen practices. She was awarded Artist of the Year (Media Art) 2017 by HKADC in 2018.
- 香港藝術館
- 策展人
- 香港藝術發展局
- 聲音藝術
- 考古
- 劇場
- 音樂
- 科技
- 藝術教育
- 藝術研究
- 大眾媒體
- 實踐
- 鮑藹倫
- 歷史
- 文化
- 戲劇
- 超8毫米
- 設計
- 參與
- 科技的哲學
- 反烏托邦
- 應用程式
- 斯坦·布拉哈格
- 直播
- 庫存
- 攝影機
-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 新生物學
- 混合現實
- 演生
- 數碼詩歌
- 自我組織
- ActionScript
- 神經機械學
- Ken Rinaldo
- 監控
- 機器
- 藝術史研究學者
- 媒體藝術家
- 自動書寫
- 學者
- 社群治理組織
- 社會倡議者
- 滑鼠導航
- 微敘事
- 翻縣空
- 藝術教育工作者
- 電子藝術雙年展
- 實驗文學
- 黃照達
- 實驗劇場
- 全球定位系統
- Daniel Howe
- 編程
- 衍生藝術
- 數據
- 運算藝術
- 鍾緯正
- 羅海德
- 林欣傑
- 電腦科學
- 創意媒體學院
- 文字機器創作集
- 錄映太奇
- 電影
- 白南準
- 微波國際新媒體藝術節
- 行動主義
- 互動性
- 文化研究
- 動畫
- 裝置藝術
- 媒介
- 起點
- 對話
- 媒體考古